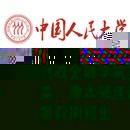在澳洲留学学生介绍他在澳洲生病看病的经历。
这次上火非同小可,其实可以追溯到7月份我从国内回来后,喉咙发炎,嗓子哑的讲不出话;喉咙好了,嘴里开始溃疡,疼得半张脸都不敢动;溃疡好了,眼睛又有毛病了。看到外面阳光灿烂,每天在家呆的无聊至极,真想赶快出去走走。但是看到镜子里的自己,眼睛肿的像猪一样,出去必定有碍观瞻,即使戴上墨镜也怪怪的,只能乖乖的在家呆。随时随地拿着我的小镜子,一会看一眼,仿佛一会的工夫眼睛就会有什么明显的好转,结果在家里做什么都不安心。顿时觉得好重要,做一个的人比什么都幸福。
就这样呆到周五,虽然眼睛有了明显的好转,但是,能去学校上课依然是个奢侈的要求。于是,我再也坐不住了,决定去看医生。心里庆幸两周前自己刚刚把过期的海外学生续了,否则,看病,对于我们这些海外学生,将是一比不小的开支。下定决心去医院时已经是周五的下午,因为担心医院也许会早下班(后来有人告诉我澳洲医院是全年不关门的,我疑心只是急诊室才会如此负责),我心里着实有些着急了。而且,我对澳洲医院的效率之差早有耳闻,只怕这一去,挂号加等待,还不知道要在医院里呆到几点才可以回来。倘若真的像他们说的“要动小手术才能把眼里的脓挤出来”,我是不是要蒙着纱布回家?所以,我不假思索的给自己觉得最可以依赖信任的朋友打了电话,希望他们中有谁可以陪我一起去看病。我知道,那天下午他们在一起玩羽毛球。我百分百相信他们不会让一个眼睛有疾的朋友独自去医院。
但我把自己的要求想得也太简单,太理所当然了,电话那端,我那吞吞吐吐的朋友显然不想从尽兴的玩乐中抽身出来陪我去看病,又不好意思直接拒绝我可怜巴巴的请求,气氛顿时尴尬而清晰。自己要求已出口,对方反应冷淡,明白的人都会就此打住。要长大成人,务必要学会不把希望寄托的在别人身上。我礼节性的说打扰了,我自己也没问题的,而后道谢,收线。站在空荡荡的路口,手里握着电话,看看通讯录上几十个电话,突然觉得这个时候,自己竟然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朋友。其实,哪怕我的朋友会再把电话打回来,用关心的语气再问我是否确定自己可以去,我也会觉得有一丝安慰。但是,没有人打回来。谁也不怪,自己做人失败选6耘笥训氖潜厝坏模踔劣行┢撸牵睦锞挂材涿畹男朔芷鹄础N叶宰约核担也恍抛约毫∫部床涣耍龉曛凶约鹤龉氖虑橐日飧丛拥亩啵〖堑霉谝桓鲆煨院糜阉倒沂悄侵帧凹词古吭谀抢锟薅既萌司醯梦沂歉龊芗崆康娜恕薄S惺焙颍也蝗衔杂谝桓雠⒆佣裕馐歉鲇诺恪?/P>
但是,困难不会因为决心而减少。即使去最近的RYDE HOSPITAL看,也要乘BUS坐上几站,希望我知道在那里按铃下车。看看表,已经是下午4点,我甚至想打个TAXI去算了,只要别去晚了。就这么想着往车站走,在路上碰到不是很熟的一个香港女生。她问我去哪里,我说去医院,并十分不情愿的把自己那只墨镜下的怪眼SHOW给她看,她大惊,说那是一定要看医生的。不过,她告诉我附近有家MEDICAL CENTER,那里也有医生,虽然不知道能否治我的眼睛,不过,应该去问问。而后她很关心的陪我走到那家在SHOPPING CENTRE里面的MEDICAL CENTER(让我称它为“门诊”),还问我要不要她陪我等着挂号,看病。我说已经很谢谢你了,不用了,她一再问我是否SURE,我说我自己可以,她才离开。突然觉得好讽刺,一个不熟的同学竟比一个相处很久的朋友要关心自己!
挂号处的小姐把我的情况大概记一下,告诉我挂号要30元,做出收钱的姿势。我突然发现自己没有带MEDIBANK CARD,她说没有卡没关系,下次复诊的时候带来告诉她就行。。在她为我建了个病历一样的FILE的时候,我告诉她我有足够的现金,她却让我坐着等医生叫我,我很奇怪为什么她再管我收钱。我这才有工夫仔细打量这间不是很小的MECICAL CENTER。设在SHOPPING CENTER的一个入口处,显然是方便那些行动不方便的病人(谁愿意在胃痛或摔伤的时候再去爬楼梯去看病?);环境宽敞,接待处不是国内的小玻璃窗口,挂号者要俯下身子,把单子什么的从小口递进去,而是像大饭店前台,台子上摆着各个医生的名片夹;等待者坐在中间舒适的大沙发上,墙上吊着电视,茶几上摆着各种杂志和社区杂志,墙边有饮水机,大厅一角是个PHARMACY(药房)。
一个医生走到前台,我听到刚才接待我的小姐在跟他讲我的眼睛的问题。他拿了我的病历,叫我跟他去他OFFICE。医生是个中年男子,灰头发,很和蔼。我终于摘了我的墨镜,他皱了皱眉,开始问我问题,我尽可能的用有限的医学英文告诉他我眼睛发炎,红肿的经过。他轻轻翻了翻我的眼皮,用一小束光照眼睛里面,而后在我病历上写了点东西,在里输了几行字,告诉我他要在我眼上扎几针,把那个特别硬的脓块挑破,把脓挤一下,但是要很疼,问我可以吗。而后,他问我对什么什么过不过敏,他要给我开一些消炎药。我没听懂那个词是什么,如果是青霉素啊什么的,我就不会过敏,我就告诉他没问题。末了,他问我是自己来的吗,有没有开车,可以自己回去吗。我说没问题。他说他去准备一下手术。
我从他的办公室被叫到另一个有些床铺和隔扇的地方,估计是这里的手术或包扎室什么的。旁边的床上靠着一个愁眉苦脸的女子,手臂上吊着绷带。医生戴了手套,让我平躺下,一会儿,拿了一只针头过来。我一下子觉得有些紧张,也不敢看是什么样的针就把眼睛闭上了。他开始翻我的眼皮,我本能的老想闭上,感觉眼皮上的皮肤都紧张起来。他说,可能会要疼一下,但是要我千万不要动。我明白,自己要是乱动,眼睛就危险了,于是两只手紧紧的抓住两侧的床单。他翻开我的眼皮,一下子,我清晰的感到有尖锐的东西扎到眼皮下的脓块处,大气也不敢出。而后,他对着刚才扎的地方,用手指使劲的挤,疼的我快喊出来了。我觉得真的有液体从眼睛里流出来,不知道是眼泪,是血,还是浓。他把一块药棉按到我眼睛上,叫我按着。一会,他换了针头,要给我扎第二针。也许那个浓块真的太硬了,这次他扎了好几下,我觉得他实际上在用很笨拙而原始的方法在挤压我的眼睛,让浓流出来。但是,我快疼的受不了了,汗都出来了,又不敢动。好容易,他递给我一块大药棉,要我按住眼睛,说,只能挤到这个地步了,不过,我一定会觉出明显的好转的。然后他递给我一张纸,说要我去外面的药房去拿药水和消炎药,然后回来包扎一下眼睛,两天后要再来复诊,看看情况是否真的好转了。
我出去把单字递给PHARMACY里的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她看起来十分活泼,问我眼睛怎么了,而后做出十分的同情的表情。然后按处方给我开了药。药的外包装上贴着刚刚打印出来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还有处方的医生的名字,她指着上面的字给我读了一遍。这次,我付了25块钱药费。
我拿着刚开的药水回到刚才的手术室,医生已经不在了,一个中年女人好象是负责的护士,接过我手中的药水。她给我的眼睛滴了药水,盖上一片棉垫,很夸张的用胶布斜斜的贴住我半边脸,固定住棉垫。我看起来一定像小时候看的动画片《黑猫警长》里的“一只耳”老鼠或其他电影里的独眼龙。我有点担忧的问她,我觉得眼睛里好象还有什么东西格着,并没有彻底挤出脓,她告诉我不可能完全挤干净,但是她保证我一定会明显的感到好转的。
走出门诊,我看到路人都向我投来奇怪的目光,我半边脸被胶布缠着,看上去像受了很重的伤,比如,跟人打架之类的。我倒没有因此不好意思,我觉得这样包扎着出门,比别扭的戴着墨镜出门要好的多。只是,我现在只能用一个眼睛来看路,视野明显小了很多,加上近视,眼前一片模糊的走回了家。我在心里暗暗下决心,等眼睛好了,一定好好珍惜,好好保护。
后来,两天后,我的眼睛真的很明显的好了。但是我没有再去看医生,我知道没有必要了。因为自己从小什么事情都喜欢讲给妈妈听,我在打电话回家时不留神把眼睛的事告诉她了,惹的爸爸妈妈一阵紧张。尽管我一再告诉他们我的眼睛真的快好了,他们还是十分担心,第二天一早就打长途给一个在悉尼的叔叔,让他开车过来看看我的“真实情况”。我的明显好转经过那位叔叔的描述传到爸爸妈妈耳朵里,他们这才放心了。我的同学说我“不该把生病的事情告诉家里”,我也后悔自己的不懂事。这个道理我不是不明白的,出国那么久,相似的事情也瞒了几次了,就怕家里人多想。而这一次,我是真的感到自己的脆弱。那天被针扎眼睛最后几下子的时候,我简直快疼昏过去了,我好希望可以抓住朋友的手而不是床单;站在路口的我,真的很难过,不为别人,为自己。其实,病痛是不怕的,最可怕的是内心深处的孤独。从爸爸妈妈那里,我可以得到理解和鼓励。惭愧的是,我却让他们为我担心了。
现在写出来我当时的感受,也绝对不是为了争论对错,也许是为了渲染一下我生病时的焦急心情吧;我跟我的朋友,依然一起吃饭,聊天,但是,我忘不了自己一刹那的无助和失落。我常常想,什么时候自己可以不再只想到自己,不再多愁善感,什么时候自己可以在生病的时候有着成人的坚强呢?
于是想告诉像我一样,以前或现在常常被人照顾的年纪轻的朋友们,出了国,一定要好好爱护自己,照顾自己,更要学着要一个人坚强的面对困难。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的更好,我们爱的人才可以的更好。
本文章关键词:澳洲留学 留学预科 澳洲留学预科
留学114为您提供更多出国留学,国内留学预科更多信息www.liuxue114.com